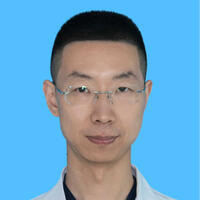张立民医生的科普号
- 精选 医生,“我耐麻药,给我多打些麻药!”
前两天30多岁的美女小丁,需要进行面肌痉挛的微血管减压术。麻醉即将开始之前,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以为自己的飒爽英姿,迷得小丁非要和我表白,结果小丁跟我说,“医生我耐麻药,一定给我多打些麻药!”。让我哭笑不得之余,也感叹人们对医学知识的匮乏。不过为了宽慰她,我还是开玩笑的跟她说了一句“别说你这小体格,来头大象我都给它麻倒”后,迅速的将她带入了梦乡,并在美梦中顺利完成了手术。作为麻醉医生,经常会得到有许多患者在麻醉前的反复“叮嘱”,一定要多给他们些麻药,不过麻药真有耐药一说吗?麻醉方法分为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所谓全身麻醉,通俗来说就是指通过各种“迷药”让你睡着。而局部麻醉除了包括俗称的“半麻”,还包括类别繁多的神经阻滞。随着麻醉技术和麻醉理念的不断进步,往往手术过程中不会采用单一的麻醉方法,更多的是采用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复合的方法,这样既可以达到更为满意的麻醉效果,又可以充分的为患者进行良好的术后镇痛。那么再回到小丁的疑问,麻药真有耐药一说吗?全身麻醉药物都是严格按照病人的“理想体重”进行估算的,然而理想体重跟各位的体重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由身高计算得出的,如果高度相同的胖人和瘦人,基本上用药剂量不会差别太大。当然,如果你是个肌肉男,或者你的酒量很大,我们会在让你入睡时,稍微增加一些药量,以保证能够迅速把你“麻倒”。在病人完全由清醒到入睡的麻醉诱导后,我们再根据监测得到的血压、心率、麻醉深度指数等各种指标进行手术中维持剂量的调整。所谓对麻药耐药一说,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们有各种监测手段来保证你绝对处于深度睡眠和无痛之中。而局部麻醉除了在产科麻醉单独应用以外,已经越来越多的复合应用在全身麻醉中。过去因为神经阻滞不全而在手术中产生的疼痛感,使人们误以为对麻药“耐药”导,然而如今麻醉可视化时代的到来,使得这种“耐药”越来越为少见。比如在小丁的麻醉中,我们首先通过全身麻醉的方法使小丁入睡,同时应用超声这只眼睛进行了耳颞神经、枕大小神经阻滞,保证了良好的术后镇痛,使得小丁从手术开始到出院,发现根本没有原来想象中“关羽刮骨疗毒”的痛苦。当今外科手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麻醉医生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让你舒服的在手术期间做个美梦,还要术后让你安全的从美梦中醒来,参与到你术后的康复管理中,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4178人已读 - 精选 围术期“片面”实施肺保护通气措施是危险的---原创
全身麻醉的病人在进行外科手术后,大概有5%~10%的患者会发生术后肺部并发症。在实施腹部外科手术的患者中,由于术中膈肌的限制,术后的疼痛等因素,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则会高达9%~40%[1]。如此高的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促使我们麻醉医生不断的寻找各种保护措施来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生的发生。 那么如此高的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原因究竟合什么相关?术中机械通气、失血、感染、术中液体输注过量以及器官的缺血与再灌注都是相关的危险因素。术中机械通气造成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原因主要包括四点:1)过高的潮气量导致肺泡张力过高;2)频繁的吸气呼气导致肺泡重复开闭造成的肺泡-细支气管连接处损伤;3)过低的潮气量导致不稳定的肺单位复张障碍;4)气道压力过高。以上因素都能够导致炎症因子的释放,而机械通气既可以恶化炎症因子的进一步释放,又可以作为初始因素释放炎症因子。 现在我们麻醉重症界非常流行的一种肺保护通气策略是基于标准体重的小潮气量通气法,即<8ml/kg。这项研究最先始于ICU中ARDS的患者通气模式受益于小潮气量的通气策略,后来被逐渐引入围术期的通气管理,也同样被证明减少了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特别是对于肥胖患者和女性患者。从2006年到2010年,超过10ml/kg的通气概率由28.5%下降至16.3%[2]。于是乎,这种小潮气量的通气方法被传呼其神!可是事实果真这么如此吗?在2014年发表在BJA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6-8ml/kg的小潮气量通气策略证明会造成术后患者30天内的死亡率增加,与此同时,进一步发现被纳入研究的这些患者旨在术中接受了较小呼气末正压(median PEEP=4)[3]。 由此可见,单纯的小潮气量不但不会对患者有益,而且会增加患者的死亡率。看到这个噩耗后你是不是想回归到原来的10ml/kg的设定中了呢?据调查,实际麻醉期间通气管理中,应用PEEP的麻醉医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我们常常满足于良好的血氧饱和度和血气结果。随着麻醉医生向围术期医生的角色转变,我们应当更注意术中的各种策略是否会对患者术后的恢复造成影响。小潮气量的肺通气固然是美好的,但是所造成的低通气肺不张会导致肺泡在反复开闭过程中超微结构发生改变,造成肺部上皮和内皮细胞的损伤,促进炎症介质的释放。虽然至今为止对围术期肺通气策略尚未达成统一的定论,但现阶段被认为是表较完整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则是:小潮气量通气(6-8ml/kg,理想体重),适当的PEEP(6-8 cmH2O),术中不少于两次的膨肺(至少在插管后和拔管前)[4]。 那么让我们行动起来,别被围术期表面“良好”的氧合数据迷惑,不要再实施片面的保护性通气模式,将完整肺保护通气策略实施起来!图为作者在日本冈山大学附属医院作为临床修炼医师参与肺移植麻醉团队(作者:张立民,沧州市中心医院麻醉科)参考文献1. Khuri SF, Henderson WG, DePalma RG, et al. Determinants of long-termsurvival after major surgery and the adverse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Ann Surg 2005; 242:326–341.2. Jaber S, Coisel Y, Chanques G, et al. A multicentre observational studyof intraoperative ventilatory management during general anaesthesia: tidalvolumes and relation to body weight. Anaesthesia 2012; 67:999– 1008.3. Levin MA, McCormick PJ, Lin HM, et al. Low intraoperative tidalvolume ventilation with minimal PEEP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BrJ Anaesth 2014;113(1):97-108.4. Futier E, Constantin JM, Paugam-Burtz C, et al. A trial ofintraoperative low tidal-volume ventilation in abdominal surgery. N Engl J Med2013; 369:428–437.本文系张立民医生授权好大夫在线(www.haodf.com)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1968人已读 - 医学科普 医生,你给我吸的是迷药吧?---和大家谈谈“迷药”
圈子外的朋友每次听说我是麻醉医生的时候,都会提及一个让我哭笑不得桥段,问我是不是拥有被歹徒用毛巾一捂就晕倒的那种迷药。前两天,单位的一个家属做手术,20来岁的小伙子,醒来之后,一直感慨我把面罩往他脸上一放就啥也不知道了,问我给他吸得什么“迷药”。其实至今为止,麻醉学界还没有开发出任何一种吸一两口就能睡着的“迷药”。所谓的“迷药”,专业术语应当是吸入性麻醉药,现在最常用的是七氟烷和地氟烷。如果单纯的用这些药物让一个成人晕倒,保守估计,至少你得吸上五分钟才能晕倒,而且除了七氟烷之外,其他的吸入性麻醉药的味道都极其难闻。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如果歹徒能一下子把你“迷倒”,请把歹徒介绍给我!那么为啥那个小伙还说我怎么一把面罩放在他的脸上他就晕倒了呢?其实放在他脸上的面罩里面只有氧气,我实际上通过输液的方式,向他的血管中推住了静脉麻醉药物,起效时间非常快,在数秒内就能把你带入到梦乡!所以,如果“有幸“被麻,面罩中可不是什么迷药哟!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7363人已读 - 医学科普 都是“牙垫”惹的祸?!
医学生经常感叹国产医疗剧的各种脑残,记得前段时间热播的《妇产科男医生》中的一个片段,因为麻醉医生不能及时到位,产科医生被迫局麻进行剖宫产,患者居然在局麻之后睡着了!美剧《实习医生格蕾》如今连播已经度过了13个年头,每当看到美国医院的患者在气管插管后居然不放牙垫,也不由得感叹编剧苏珊大妈也成“脑残”,而且在日本作为临床修炼医师后,发现气管插管的患者居然也不用牙垫,彻底颠覆了我的“价值观”。那么牙垫究竟放还是不放呢?总体来说,支持不放牙垫的理由主要有:1.牙垫的放置会使得口腔持续性开放,造成口腔黏膜干燥,唾液减少,口腔的自净作用和局部能摸抵抗力减弱,大量细菌在口腔内繁殖,从而引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已有证据表明,去除牙垫后能够使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降低30~50%;2.牙垫的放置造成口腔内部黏膜的损伤,如术后的口腔溃疡,还会增加口腔不适感,下颌关节的酸胀疼痛。原来很多术后的肺炎,口腔溃疡和下颌疼痛都是牙垫惹的“祸”!如今在国内绝大部分医院,依然气管插管后选择放置牙垫,国内的麻醉医生的担心主要是患者可能会有咬管的情况。但既往的研究表明,患者苏醒后咬管的情况发生率极低,因为在咬合后由于患者无法通气,会迅速松开闭合的牙齿;另外,这个担心完全可以在术毕前短时间放置牙垫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型气管导管由于内部存在钢丝,咬合后可能后造成气管导管不能复位,一定要在术毕前放置牙垫。麻醉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对患者的预后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应用循证医学的证据,改变点滴!麻醉医生张立民公众号致力于麻醉科普、前沿介绍,以及生活杂谈,欢迎大家阅读!张立民,医学博士沧州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日本冈山大学O-NECUS交换生笹川医学奖日本临床修炼医师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3441人已读 - 医学科普 你属于潜在的气管插管困难的人群吗?
自己做麻醉医生以来,养成了两大职业病:一个是看到陌生人之后,会在内心默默的估算一下他的体重,另一个就是就无意识的看看他的是不是困难气道。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大鹏,就是传说中的“小下巴”脸型,医学上称之为小下颌,就属于麻醉医生比较头痛的困难气道。不过,究竟什么是小下颌呢?通俗的讲,如果从下巴尖到我们喉头的距离小于6厘米,我们就称之为小下颌。一般用我们的手来比划一下,就是四个手指头的宽度(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去比划了一下,嘻嘻),如果你小于这个距离,恭喜你进入了潜在困难气道的行列!门牙向前突出,脖子活动不良甚至固定,张不开嘴,这些也都是困难气道的危险因素。即使你有上述的这些特征,你也无需恐惧,近年来发展了越来越多的电子可视化气道工具,使得麻醉医生有了武装到牙齿的装备来对付这些困难的气道!前几天,自己就刚刚成功地应用这些先进装备处理了一例强制性脊柱炎,颈部不能活动,下颌距离仅有两指的患者。记得在日本留学时,一个住院医师以肥胖为引由,简单的对困难气道进行了总结。当时我对这个住院医师和他的上级医师提出质疑,因为循证医学证据表明,肥胖并不是困难气道的危险因素。所以各位体重稍微大一些的朋友,你们也不必因为自己的体重担心可能属于困难气道了。困难气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醉医生没有预料到困难气道,结果没有事先准备好各种对策和工具,造成可怕的后果。因此,选择有经验的麻醉医生也为我们得生命添加一道保险!麻醉医生张立民公众号致力于麻醉科普、前沿介绍,以及生活杂谈,欢迎大家阅读!张立民,医学博士沧州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日本冈山大学O-NECUS交换生笹川医学奖日本临床修炼医师本文系张立民医生授权好大夫在线(www.haodf.com)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1893人已读 - 医学科普 “我怎么醒了之后总是嗓子疼?”---气管插管
前两天,老同学大鹏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以为又是结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瘪瘪的口袋,准备又得省吃俭用几天了。结果却跟我咨询起了专业问题,他说明明做的是眼睛的手术,为啥醒了之后总是嗓子疼?我说你是不是做得全麻?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并告诉他“你这脸型是标准的小下颌,麻醉医生给你做气管插管时候肯定费了一番力气,可能损伤到咽喉的黏膜了,吃两天金嗓子就没问题啦”。明明做得眼睛的手术为何要做气管插管呢?!这要从全身麻醉的必须药物之一肌肉松弛剂说起。所谓的肌肉松弛药物,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的骨骼肌松松的,以便于手术操作。既然肌肉变得松松的,负责我们呼吸的肌肉变得松松的之后,也就不再听从大脑的指挥进行有序的收缩和舒张,需要我们借助呼吸机来帮助我们中呼吸。这时候就需要气管插管这个媒介将我们的呼吸系统和呼吸机相连接。所谓气管插管,就是将一根空心的管子经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声门,最终进入到气管中。如果在进入过程中碰到了周围的黏膜组织,就有可能造成术后的嗓子疼。当然,气管插管不局限于使用肌肉松弛剂的情况,还应用于急救、呼吸支持等方方面面,是一名临床医生应当必须掌握的操作。由于麻醉医生在临床工作中进行这项操作的频率是最高的,也成为了该项技术的专家。但是气管插管失败却是麻醉医生的噩梦,因为如果不能及时建立有效的通气媒介,患者就有可能由于窒息死亡,所以在麻醉知情同意书中往往第一项就写到“困难气道可能会导致死亡”。昨天下夜班,值班碰到了一例疑似发生儿茶酚胺风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夜班值得我稀碎稀碎的……明天会和大家介绍下什么样的人可能有气管插管困难的风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麻醉医生张立民的微信公众号!麻醉医生张立民公众号致力于麻醉科普、前沿介绍,以及生活杂谈,欢迎大家阅读!张立民,医学博士沧州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日本冈山大学O-NECUS交换生笹川医学奖日本临床修炼医师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1.2万人已读 - 医学科普 “我怎么觉得自己做完全麻之后,变得傻傻的?“
经常有朋友和我说,经历过全麻之后,总感觉自己变得傻傻的。我说你不是变得傻傻的,而是变得萌萌哒!那么究竟麻醉药物会不会对你的记忆能力产生影响呢?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下全身麻醉究竟用了哪些药物。镇静药,镇痛药和肌肉松弛药是全身麻醉必不可缺少的三种药物。其中肌肉松弛药是作用于外周神经的,不会对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任何作用。而镇痛药的神经毒性一般认为是极其罕见的,报道较少,仅有一些个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认为可能会对智力发育产生影响的药物是镇静药物,包括吸入性的麻醉药物和静脉麻醉药物,种类繁多。现在已证明在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完全的成人中,镇静药物不会对神经产生明显的损伤。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上亿的神经细胞,每分每秒都有死去的神经细胞,这些麻醉药物不会对这种正常的生理过程产生任何的干扰!但是干货来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正在发育的儿童或退化的老人,目前研究结果是可能有影响。一些老人在接受大手术后,学习能力、记忆力和注意力短期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数天后可恢复正常,而极少数人数月甚至永久都无法恢复[1, 2]。所以现在我们推荐小儿在4岁以下,一年最好不要接受两次和两次以上的全身麻醉;对于老年患者,也尽可能的使用局部麻醉复合全身麻醉的方法,减少全身麻醉药物的应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近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也发现,小剂量、短时间的吸入性麻醉药物能够产生非常显著地神经保护作用,所以我经常会在有严重脑损伤的患者中加入适量的吸入性麻醉药物。万物平衡的原理在麻醉药物的使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使用的过多会导致敏感人群的神经损伤,使用得当则会产生神经保护作用。关于吸入性麻醉药物和静脉麻醉药物的药理作用至今还没有完全探索清楚,也值得各位同道一起继续前进和努力。[1] B. Backeljauw, S.K. Holland, M. Altaye, A.W.Loepke, Cognition and Brain Structure Following Early Childhood Surgery WithAnesthesia.[2] V. Biddle C Fau - Ford, V. Ford, TheNeurotoxicity of General Anesthetic Drugs: Emphasis on the Extremes of Age.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1.6万人已读 - 医学科普 全身麻醉药物对小儿智力发育的影响
在麻醉技术诞生之前,哪怕是阑尾炎这样简单的手术,在当时都不啻于以命相搏。时至今日,麻醉带来的益处早已获医患双方所公认,而手术亦成为一种常规治疗手段。麻醉为诊疗带来的优势使其愈加广泛地应用于婴儿及学龄前儿童,与此同时,麻醉的安全性也越来越成为麻醉医生、政府及公众所关注的问题。早在20多年前,研究者便开始注意到全身麻醉药对神经结构和神经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怀孕大鼠长期连续暴露于亚临床剂量的氟烷时,其幼鼠的中枢神经系统会有发育延迟的现象。之后的一系列动物实验发现,发育中的哺乳动物(包括大鼠、小鼠、豚鼠和灵长类等)的脑组织在麻醉药物作用后,有可能发生神经元凋亡和神经变性。传统观点认为,全麻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可逆,麻醉过后即可恢复到麻醉前的状态,并无其他毒副作用。以往啮齿类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全麻药可诱发神经细胞凋亡,产生对神经系统的功能损害。然而,啮齿类动物接受数小时麻醉相当于人类新生儿接受几天甚至数周的麻醉。动物实验得出的答案不能类推到人类,但对临床仍有重要意义。目前,以评估麻醉药物对小儿神经发育之影响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临床试验主要有三个,分别是GAS研究、PANDA研究和MASK研究,三者都仍在进行当中。其中GAS研究于2015年10月在《柳叶刀》(Lancet)杂志上披露了中期研究结果,全麻组和局麻组受试者之间并未发现神经发育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全麻会较局麻增加神经发育不良的风险。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则认为,在4岁以下每年接受两次全身麻醉则对成年后的智力发育存在影响。至于儿童患者及家属应如何面对麻醉,因噎废食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毕竟,医学治疗从来都是风险与收益的统一体。本文在这里虽然不能告诉你麻醉带来的风险到底有有多大,但如果真的有一天要面临手术,听从你的麻醉医生的专业建议,大概率总是没错的。同时,如何组合麻醉方式尽可能的减少全身麻醉过程中全麻药物的剂量,也是麻醉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立民 副主任医师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麻醉科1680人已读